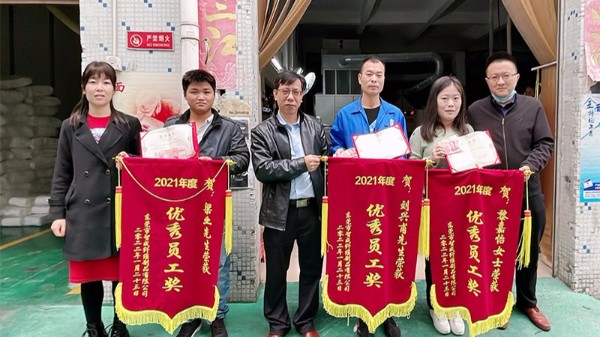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初期,紡織工業是國民經濟中的第一大產業,紡織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38%。作為紡織工業的源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化纖產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強大、從稚嫩到成熟的奮斗歷程。
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時間節點,縱觀1949~1978年我國的化纖工業發展史,基本完成了從“0
”到“ 1”的過程。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化纖設備,走的是老廠改造、技術引進,合理消化吸收,到部分設備的國產化之路;在化纖的發展品種上,一開始以粘膠纖維為主,后來發展為粘膠纖維與合成纖維并舉,初步解決了中國人民的穿衣原料問題。1978
年12 月,黨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確定了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由此,中國化纖事業也在這種利好因素推動下踏上了迅速發展之路。
從1979年至今,中國的化纖產業發展,主要經歷了如下幾個歷程:1)在上世紀70年代“四大化纖”項目基礎上,全國建立了第二批大型化纖廠; 2)開放市場、引進外資,企業產權主體日趨多元化;3)加入WTO后,化纖行業與資本進一步融合,民營化纖企業開始做大做強; 4)2014年后,在“互聯網+”的思維引導下,化纖行業的設備智能化迅速提升,生產效率得到進一步提高。
本文以時間脈絡為線索,記述了我國化纖產業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歷史變遷。
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1949~1955年)
在新中國初期,我國的農業生產不穩定,我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少,隨著基礎建設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和公路交通事業的發展,耕地面積呈現遞減趨勢,人多地少的矛盾隨著時間的發展而逐漸顯現。在此前提下,國家要解決幾億人吃飯問題,首先要確保糧食生產,但棉田面積的擴張會因此受到限制。除去這一問題,我國地域遼闊,南澇北旱的問題經常發生,棉花生產也隨著氣候的問題呈現大小年現象,而棉花的收成,又會直接影響紡織工業的生產。豐收了,紡織廠要加班加點;歉收了,紡織廠要減少班次,降低產量。綜合這些因素,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錢之光提出“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的方針政策,并且基于我國當時國情,提出優先發展粘膠纖維。這主要是基于我國的木材資源雖然不多,但棉短絨資源豐富,有利于發展粘膠纖維。但是,由于當時化工部以發展基本化工為主,粘膠纖維項目只能在時間點上后移。
1954年秋,紡織工業部成立了化纖籌備小組,著手研究化纖纖維生產建設問題。1955年9月,錢之光率領紡織工業代表團赴蘇聯考察,了解有關企業管理制度,勞動工資、產品品種質量、科學研究以及化學纖維和棉花等方面的情況,在歷時兩個多月的考察中,除了參觀紡織廠外,也參觀了一些化纖廠。回國后,紡織工業部立即開展我國化纖早期的建設工作:一是把兩個停車已久的老廠即上海安樂人造絲廠和丹東化纖廠進行恢復和改造;二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自行建設粘膠纖維廠。
上海安樂人造絲廠是民族資本建立的一個試驗廠,主機是從法國購買的設備,生產能力為粘膠纖維1噸/天,由于設備缺損,長期沒有投入生產。1956 年紡織工業部開始對該廠進行恢復和改造,到1958年正式投入生產,紡出了我國第一批粘膠纖維。
丹東化纖廠的設備原本是日本侵華時期,東洋人造絲株式會社從日本搬遷到丹東的舊設備,該廠于1941年投產,實際日產粘膠只有2~6噸,抗戰勝利前夕,又被日軍破壞,到東北解放時,已經無法生產。紡織工業部在 1955年年底對該廠修復改建,1956年5月完成初步設計,設計產能為日產粘膠短纖 12噸。1955年6月施工,
1958 年1月正式生產,達到預想的產能能力。
上海安樂人造絲廠與丹東化纖廠復工擴建工作完成后,兩廠生產能力共5000噸/年粘膠纖維,這是我國粘膠纖維生產的最初起步階段,實現了新中國生產化學纖維從無到有。
化學纖維產能擴增(1956~1962年)
1956年,紡織工業部向國務院申請,從民主德國引進年產5000噸粘膠纖維的成套設備,建設保定化纖廠;并同時引進日產1 噸的錦綸設備,在北京建設一個小型的合成纖維實驗工廠。經周恩來總理批準,1957年10月,我國第一個自己建設的大型化纖廠經過
1 年多的緊張籌備,正式動工興建,到1960年7月,保定化纖廠4 個紡絲區全部投產。而北京合成纖維實驗工廠,因規模較小,在1957年即已建成。
為了配合化纖工業發展,培養專業技術人員,除在上海華東紡織工學院早有化纖專業設置外,紡織工業部還選派一些技術人員到民主德國進修,并于1958年創辦了北京化纖學院。
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開始的化纖產業建設工作,是我國化纖工業的初建階段。雖然規模不大,但是為以后化纖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特別是保定化纖廠采用的是當時民主德國較為先進的技術裝備,為我國培養和輸送了較多的專業人才,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粘膠纖維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在我國的化纖工業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1960年7月,中央建議采用棉短絨和木材等為漿粕的原料,繼續建設一批粘膠纖維廠,所需的設備由國內自行制造。在此理念下,我國開始了以上海二紡機、榆次經緯紡機、鄭州紡機等廠自行設計和制造成套粘膠短纖和長絲的設計和制造。第一批國產粘膠短纖的設備研制成功后,在上海安達化學纖維廠安裝試生產。在此基礎上,紡織工業部從 1961年開始,陸續在南京、新鄉、杭州、吉林等地興建了一批粘膠纖維廠。與此同時,丹東化纖廠擴建了粘膠纖維車間,保定化纖廠擴建了棉短絨漿粕車間。
這批粘膠纖維廠的建設,大大提高了我國化學纖維的生產能力,奠定了我國粘膠纖維工業的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1959年~1961年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形成這種困難時期的根源主要是這三年發生了持續性的自然災害,造成了我國的棉糧等經濟作物歉收,從而導致經濟困難。但是,從史料上看,我國化纖工業的基礎,正是在這幾年打下的。這一方面體現出黨和國家對化纖產業的支持力度較大,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化纖作為一種工業產品,不會因自然災害而出現產量波動,給我國的紡織工業提供了穩定的原料,從而側面印證了 1953年紡織工業部提出發展“天然纖維與化學纖維并舉”方針政策的預見性與正確性。
合成纖維推進規模化建設(1963~1972年)
1963年,紡織工業部根據當時世界化纖技術發展的趨勢,進一步明確要把我國化學纖維搞上去,必須實行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并舉,并要以合成纖維為主要發展思路。在此思路下,我國先后從日本和英國引進了年產1萬噸的維尼綸設備和年產 8000噸的腈綸設備,分別建設了北京維尼綸廠和蘭州腈綸廠,這標志著我國合成纖維實現了量產。
1970年,紡織工業部和第一輕工業部、第二輕工業部三部合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業部,錢之光任輕工業部部長。在輕工業部成立后的國務院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宣布:“要抓輕工業,輕工重點抓紡織、紡織重點抓化纖。”這就解決了把投資重點轉向化纖建設的問題,為大規模發展化纖工業提供了保證。
同時,得益于大慶油田的迅速開發,我國的石油產量大幅度增加。1971年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國際關系經貿合作迅速發展,為引進成套先進設備提供了條件,這時輕工部提出引進成套石油化纖設備的設想。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相關文獻記載,1971年下半年,中國準備上滌綸長絲項目來源于毛澤東主席在上海的一次短暫停留。據說當年毛澤東主席在上海短暫停留期間采用社會調查法,讓一位工作人員拿著“紡織專用券”排隊,買一條“的確良”褲子,結果工作人員排了大半天的隊才買到,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毛澤東問周恩來,能不能多搞一點“的確良”的褲子,周恩來回答說“的確良”的原料是進口的,國內嘗試過用腈綸短纖紡紗試制面料,沒有成功。
但之后,周恩來將毛澤東的意見傳達給國務院業務組支持經濟工作的李先念、華國鋒、余秋里,隨后國家計委通知錢之光。錢之光寫了《關于引進成套化纖、化工技術設備的報告》,送交計委,用李先念、華國鋒、余秋里3人的名義,報送國務院總理審批。
1972年2月,周恩來親筆在這個報告上批了“擬同意,即呈主席批示。”
毛澤東主席圈閱了《關于引進成套化纖、化工技術設備的報告》,此后輕工業部內成立了成套設備進口辦公室,開啟了“四大化纖”的建設,以此開啟了我國的合成纖維規模化建設時期。
技術水平向發達國家看齊(1973~1977年)
20世紀70年代,我國陸續建成的“四大化纖”基地主要包括上海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天津石油化纖廠和四川維尼綸廠。總規模為35 萬噸/年,其中滌綸18萬噸/
年、腈綸 4.7萬噸/年、錦綸4.5萬噸
/ 年、維綸7.8萬噸/年。其中,1974~1978
年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建成; 1974~1981年遼陽石油化纖廠和四川天然氣維尼綸廠建成;1977~1981年天津石油化纖廠建成。這4
個項目的前道供需化工料的生產設備以引進成套設備為主,后道供需的化纖紡絲設備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以國內生產的設備為主。
這種“設備技術引進加國產設備”的組合,大大提高了我國化纖生產的技術水平和自給能力。合成纖維特別是聚酯方面,因為擁有日本、東德、法國等著名公司的多種技術,加上后期根據我國國情對部分設備的關鍵部位進行自主改造,使得我國在20世紀70 年代后期的合成纖維品種以及生產技術已經與發達國家的化纖生產技術差距縮小很多,能夠基本達到發達國家的化纖生產水平。
尤其是上海石油化工總廠的投建,使我國有了第一批滌綸纖維,雖然當時的滌綸產能僅有2.2萬噸/年,但是卻為全國提供了國產“的確良”面料的生產原料。同時,由于當時上海石油化工總廠的建設用地來源于圍海造地,動用了 5萬農民參與這一項目,故當時有“千軍萬馬戰金山”一說使得該項目全國聞名。
組建第二批化纖工業基地(1978~1983年)
1978年開始,紡織工業部開始組建第二批化纖工業基地。包括:儀征化學纖維廠,設計產能為53萬噸/
年的聚酯;上海石化總廠二期,設計產能為 18萬噸/年的滌綸纖維;河南平頂山簾子布廠,設計產能為1.2
萬噸/ 年的簾子線。
國務院能夠批準上述3個項目的時代背景為: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人口快速增加,此時中國的棉糧爭地的矛盾變得更加尖銳。為了解決數億人的穿衣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化纖產業,同時,一些高層領導也較有遠見地看到,發展化纖事業,不僅僅是解決國內數億人的穿衣問題,更是因為其項目建設周期短,而且可以通過其出口創匯。故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上述 3個項目批復較快。
但是在1979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階段,儀征化纖以及上海石化總廠二期工程被政府通知緩建,其主要壓力來源于資金問題。尤其是儀征化纖,在1980年,其工程所用的8000 畝耕地全部征用完畢,且引進設備的訂貨合同已經生效,即使是工程緩建的情況下,根據合同,到期也需要支付3億元用于購買設備,而工程商的征地款以及安置費,至少也要付上億元。但另一方面,當時國家每年需要花費近20
億元進口棉花和化纖原料,用于彌補紡織工業原料的缺口;如果儀征化纖廠能夠順利建成投產,那么其生產的滌綸短纖和聚酯都將完全替代進口。故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行決策,如何解決資金問題,成了紡織工業部頭疼的問題。
問題最后得以解決,得益于時任國務院總理谷牧以及時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榮毅仁先生。在谷牧的支持下,中信公司在1982年1月首次發行了100 億日元私募債券,該債券的意義在于中信首次以一個公司名義,憑借一國之力和改革開放的利好形勢,在資本主義國家發行債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天辟地的大手筆。中信公司用發行的日元債券籌集來的資金,80%投入儀征化纖的建設,紡織部也千方百計從地方籌集到兩億元,最終盤活了儀征化學纖維廠項目,該項目最終于
1985 年建成一期工程并投入生產。此后儀征化纖在一期基礎上,采用邊生產邊建設的模式啟動二期工程,至1988年6月底,儀征化纖實現利稅
11.6 億元。
儀征化纖項目,是中國化纖項目建設與資本融合國際資本的一次大膽嘗試。在這個項目上,國家用較少的投資,靠中信公司在國外發行債券和從別處借款,短短幾年就贏回了一個大型化纖聯合企業。儀征化纖項目的成功,被廣泛傳揚,并且當時被譽之為“儀征模式”。
在儀征化纖等項目緊鑼密鼓建設時期,我國的紡織品產量得到大幅度提升,特別是化纖紡織品的迅速發展,使得市場上紡織品的供求關系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其具體表現為當時我國的紡織品在總量上已經能夠較好的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在這種時代背景下,1983年12月,在紡織工業部與商務部的多次共同建議后,國務院決定取消布票,棉布敞開供應。這是紡織工業以及化纖工業在解決人民穿衣方面取得的一個重要標志性成果。同時,這也給市場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紡織產業政府管控會越來越少,正是從此時開始,化纖產品的經營逐步由政府管控向市場化轉型,這種轉型,為中國的化纖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與動力。
民營、三資企業陸續涌現(1984~2000年)
1984年開始,化纖行業開始出現外商投資建立化纖“三資”企業,當年項目總數為9個,協議外商投資金額1321 萬美元。以此為標志,化纖行業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其企業性質不再是單一的國有企業,其后幾年間,化纖行業陸續出現了民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資企業。伴隨著這些企業的出現,化纖行業對利用外資問題的爭議開始增加。一種看法認為國內沒有資金能力,就應該全方位開放市場,積極吸納國外資金;另一種看法認為,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將搶占中國市場,損害國內化纖企業的利益。爭論最終以開放市場,積極引進外資、化纖設備、化纖技術告終。
20世紀90年代開始,許多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大規模投資,化纖領域中的外商投資公司有:美國的杜邦公司、阿莫科公司,日本的丸紅、東麗、帝人、三井等商社,德國的巴斯夫公司,韓國的曉星公司,中國臺灣的遠東、翔鷺、臺塑集團等。這些外資企業的加入,豐富了我國化纖行業的品種,也通過其帶來的技術加速了我國本土化纖技術的提升。
但是,隨著外商投資化纖領域比例的增加,使我國化纖工業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更為艱難的處境,特別是國有企業。我國企業無論是產品出口,還是國內銷售,都存在更加激烈的競爭。1990~1995年期間,一些外資企業利用政策優惠,以低原料成本和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形成了局部壟斷,產品在國內低價銷售,擾亂了國內市場,影響了同類企業正常的生產和銷售。如
1995 年春夏之交,某大型獨資聚酯纖維企業突然大幅度低價傾銷,造成聚酯長絲價格短期內大幅度下滑,國內長絲廠家紛紛停產、減產,經濟效益急劇惡化,個別企業甚至瀕臨破產、倒閉。
1995~2000年期間,尤其是1996年之后,紡織行業開始了壓錠工作。受紡織行業的壓錠工作影響,化纖短纖類產品在這幾年間的經營也較為窘迫。在這一階段,化纖企業第一次迎來了市場的洗牌,一些國有化纖企業,在這幾年間完成了企業改革,有的變成混合型股份制公司,有的轉變成了民營企業。中國化纖行業,經過這 5年的變革后,開始成為世界上化纖產量最大的國家。
出口市場迎“入市”新機遇(2001~2007年)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給整個中國化纖行業帶來了一次歷史性機遇。當然,在加入 WTO初期,整個行業內對于加入WTO是“狼來了”還是“與狼鼓舞”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這種爭議的由來,主要是對加入WTO
中國化纖行業的比較性優勢所站的立場不同而產生的。比如在 2000年前后,我國的進口聚酯切片關稅是16%;聚酯短纖維和滌綸長絲的關稅率是19%
和 21%;而按照當時的WTO協議要求,到2005年,其進口關稅均要降到 6%~6.5%的水平。這樣,加入WTO后,我國的聚酯產業進口成本將大幅度降低,再結合當時我國的化纖行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產品開發能力低、產品的同質化現象嚴重、下游主要是服裝行業等客觀因素,由此得出中國的化纖產品在國內市場將受到沖擊的結論。
不過,2002~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前,我們不難發現,這段時間是中國化纖行業發展最為迅速的幾年。根據紡織工業年鑒2008年的數據,可以看出,2000 年我國的化纖產量為694.2萬噸;至2007年,我國的化纖產量為2393.1 萬噸,7年間其增長率為245%;而從中國化纖占世界化纖比重看,2000 年中國化纖總量占世界總產量的58.9%;至2007年該數據為74.1% 。歷史數據較好的說明了,中國加入WTO后,是“與狼共舞”而非“狼來了”。出現這種戲劇性的反差,筆者認為,主要得益于以下3點:
1) 中國加入WTO后,最初,業界看到的是競爭上的差距,后來一些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引進先進設備和生產工藝,彌補了這一差距。2)民營企業在這幾年間迅速崛起,比如浙江恒逸、浙江榮盛、江蘇恒力、江蘇盛虹、浙江華峰氨綸等企業均是在這段時間得到迅速發展。 3)中國加入WTO后,我國逐步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纖生產基地,轉變成了世界化纖生產基地與出口基地,而出口市場在加入WTO 后,比未加入前做的更大,這一點有很多化纖從業者始料未及。
“智能制造”成產業新優勢(2008~2019年)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席卷到中國的化纖行業,這一年,中國化纖行業遭遇了加入WTO后的第一次困難處境。所幸的是,2009 年,中國國務院推出了《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得益于該規劃,中國的化纖工業在2009~2014年期間,開啟了靠智能設備提升勞動效率的時代。
2014年11月,李克強總理出席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提出互聯網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工具;2015 年3月,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提交了《關于以“互聯網+”為驅動,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建議》的議案。得益于“互聯網
+ ”等創新項目的提案,在化纖生產上,一些化纖企業也開始了智能設備的應用。其中,浙江桐昆集團的機器人生產車間,能夠做到在滌綸長絲生產過程中的落絲、輸送、檢驗、套裝、碼層、捆帶、纏繞、貼標簽等一系列工序的自動化;新鳳鳴集團的5G技術車間,生產效率比同行提升
15% ;而用工方面則降低15%;2019年,在中國化纖協會主辦的“化纖工業互聯網與智能制造高層研討會”上,華為云攜手三聯虹普正式發布“化纖工業智能體解決方案”,以共同推動化纖及原材料行業智能化業務發展。這些企業智能制造的應用意味著,化纖行業不再是傳統認知上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其生產效率,用工量將明顯減少,同時對于行業內從事生產的人員,技術要求會越來越高。